刑法规范首先是裁判规范,刑法的适用是一门专业性特别强的工作,刑法学必然具有专业性。但仅注重刑法学的专业性还远远不够,不能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刑法理论不是好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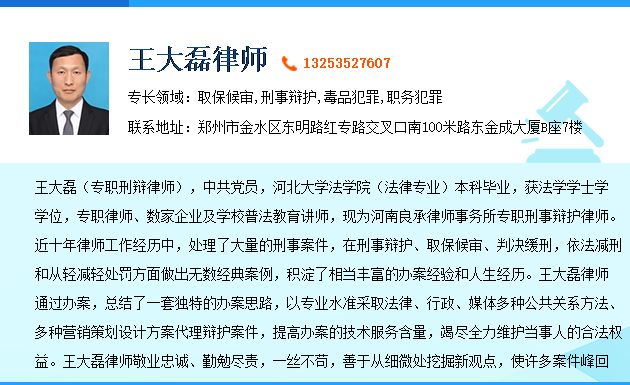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权益不断增加,需要刑法的保护;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公正文明适用刑法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刑罚机能的发挥,依赖于现阶段民众意识的认同。“如果刑罚不符合国民的‘规范意识’‘正义感’,刑罚制度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机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刑法学了解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
由于媒体的发达,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能够迅速、直接了解民众意见。民众意见对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影响越来越大。反过来说,不管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政策,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即使具有合理性也难以被采纳。例如,虽然从法律逻辑上说,鉴于死刑的弊端,在现行刑法之下,法官也可以不适用死刑;但从现实来考虑,法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现行刑法之内削减死刑,并非法官与学界可以左右,还需要民众的认同,民众认同后决策者才可能认可。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与民众沟通。
刑法规范虽然是裁判规范,但同时也蕴含了行为规范。“任何社会只有当法律得到‘自愿地’和‘自发地’遵守才能有效地运作。”只有当刑法规范充分发挥了行为规范的作用时,才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刑法学具有通俗性。
我国的刑法学承担着多项任务,既要为立法机关提供理论指导,为决策机构献计献策,为司法工作人员提供刑法适用的理论依据,也要为法科学生提供丰富的刑法理论,还要向社会一般人宣传刑法的基本内容,这些都需要专业性与通俗性并重。
第一,刑法学要实现保障人民权益的根本目的,就必须获得真正的民意。刑法学者既不能将自己的观点视为民意,也不能将不同于自己观点的民意视为糟粕。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立法不可不考虑公众的诉求,国家对国民的刑法保护,应当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我国正在发生有史以来最迅速、最全面、最伟大的变革。要使刑法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就要时刻把握民意,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心声,而不能一味追求与国民不同的价值判断。
首先,在缺乏自媒体的时代,民意由精英、媒介所建构或者是被制造出来的,因而可能与公众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但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民意调查并不困难,了解真实民意相对比较容易。网络虽然不能全面、准确反映民意,但的确是了解民意的便捷路径。此外,其他各种社会调查方法仍然行之有效。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以深度参与的方式了解民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路径。
其次,了解民意首先是了解民众的基本诉求与愿望,了解民众对相关行为的态度,了解民众态度的形成原因,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及实施对民众造成的利弊,进而总结刑法规范与刑法适用的妥当性与问题性。一项法律规范以及某种行为对民众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影响如何,民众凭借自己的切身体会与朴素的法感情就能得出结论。笔者在某地发现民众对毒品犯罪恨之入骨,许多人尤其是吸毒者的家属、亲友强烈要求处罚代购毒品的行为。是否听到这样的声音,必然影响对代购毒品行为性质的价值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如何适用,也要倾听民意,以人民群众的常态生活事实与基本价值观念为根据,否则就会偏离法律制度的宗旨。例如,在一段时间,司法人员要求民众在面临不法侵害时报警和退让,将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的警告作为认定相互斗殴的根据,将防卫人造成的轻伤害认定为防卫过当,进而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犯罪,既背离了民众的价值观念,也不符合常情常理;不仅未能实现保护人民权益的目的,而且不当限制了民众的防卫权限。反过来说,只有了解民众的生活事实和尊重民众的基本诉求,才能合理地认定正当防卫。此外,虽然刑法学的技术性问题不可能根据民意决定,但对价值判断方面存在重大争议的具体问题(如应否处罚不能犯、偶然防卫等),都可以通过了解民众基于正义的直觉得出的结论来检验相关的理论学说。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自19世纪末对非理性人的发现,民意的难题日益突显,例如,易导致多数暴政、易受宣传影响、易受制于少数精英等。”在当今媒体化时代,“媒体对于刑事司法的影响整体来看是负面的,它放大了犯罪问题,并且大肆宣传社会需要越来越严苛的刑事政策”,导致民众常常是为了获得安心感而主张严苛的刑罚。但是,“‘安心感’这种社会心理,是受到媒体与时代风潮强烈影响而形成的不安定感觉,未必存在合理根据。在国民的不安欠缺客观事实佐证的场合,能够消除这种不安的有效方法不是刑事立法,而是对真实事实的报道。”既然通过对真实事实的迅速报道就足以保护国民的安心感,就没有必要动用刑罚手段。显然,刑法学必须区分媒体意见与真实民意,进而得出妥当结论。
第二,刑法学者要善于与民众沟通,使民众接受具有普遍性、进步性的法理念。
当下,刑法学者的部分观点与民意存在明显的对立。当网民对某个案件形成压倒性意见后,即使刑法学者认为某些网民意见并不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也基本上保持沉默。虽然不能认为刑法学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但应承认的是,部分民众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接受具有普遍性、进步性的法理念。所以,刑法学者需要与民众沟通。
例如,民众常常特别憎恨犯罪,因而主张从严打击各种犯罪。刑法理论倘若单纯从学理上论证重刑主义的弊端,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对此,只能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讲理。例如,美国学者针对美国的严打措施指出:“近几十年对于犯罪的‘从严’措施对犯罪率的降低仅起了一点点作用,却花费了数千亿美元。除了花费巨大和收效甚微之外,‘从严’措施的核心内容即大规模的监禁措施也带了很多问题。”倘若我国也有相关的实证数据,相信也可以消解民众的重刑主张。
再如,刑法学者一般主张严格限制甚至废除死刑,但民众可能处于死刑的迷信中。刑法学者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就必须与民众沟通。德国废除死刑的主要原因是纳粹时期令人震惊的滥用死刑的事实,以及二战后民众明确拒绝死刑。法国的罗贝尔·巴丹戴尔意识到废除死刑之所以困难,非理性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民众对罪犯要求“处以死刑的狂热”之中,所以,他积极参加为支持废除死刑而组织的报告会,以大量国际性调查作为依据,竭力证明凡是废除死刑的地方,血腥的犯罪率并没有增加,犯罪有它自身的道路,与是否保留死刑毫无关系。他还写了许多文章,在电台与电视上就死刑问题发表谈话。实际上,“法国废除死刑时百分之六十的法国人反对,但政治精英们说服了民众,重新奠定了社会的法律文化基础。”我国学者应通过实证研究向民众说明死刑的消极后果,使民众不迷信死刑。
第三,刑法学者应当撰写通俗性读物,面向社会大众举行刑法学讲座,普及具有普遍性、先进性的法理念。
刑法规范虽然蕴含行为规范,但不可能期待所有国民阅读刑法典与刑法学论著。“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将一本考古学的或文学史的书放在礼品桌上,但很少放一本法学书籍,即使这本法学书籍可能对读者的知识没有提出特殊的要求。”一些人会由于不懂历史、文学等知识而感到羞愧,但不会因为不懂法而感到内疚。可是,法律又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用法理念指导日常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日本有许多著名学者撰写通俗刑法读本,《刑法入门》《刑事法入门》之类的书籍并不少见,这类书籍能让一般人了解刑法;许多学者也会面向社会大众举办刑法讲座。我国刑法学者也应当这样做,以便普及具有普遍性、先进性的法理念。再如,日本实行陪审员制度以后,刑法学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使刑法理论更为简化、通俗。在我国,“司法改革以后,程序进程迅捷,且陪审员参与审判,此时刑法理论不能太抽象,过于专业、生僻的术语应尽可能减少,太复杂的理论要尽可能交代得简洁。换言之,原来面向刑法教授、专业法官、检察官的刑法理论,现在要面向陪审员,面向被告人,若刑法理论还朝着很复杂的方向去发展,司法改革就很难进行。”总之,“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应当成为刑法学者的努力目标。
顺便指出的是,刑法学者应多撰写适合本科生阅读的“通俗”读物。法学的重心是教育而不是研究;法学教育不能只注重少数,而应注重绝大多数(应当注重培养本科生)。可是,迄今为止,一直少有适合提升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适用技巧的“通俗”作品,也基本没有以本科生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学术刊物对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的比拼仅对少数人有意义,对培养本科生几乎没有作用。不管研究水准多高,只要不能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法科学生,法学就是失败的。只有全面提升本科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与法律适用水平,才有可能全面提升刑事司法能力,树立刑事司法权威,进而使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形成良。
